暮春时节,从高邮到龙虬庄的路上,窗外的树木、房舍、河流,以及路边不知名的野花开得很灿烂。
早在1994年,我的兄长肖维琪就带着我和文友昇明,去过龙虬庄——当时叫一沟乡红胜大队,在考古挖掘现场,我们看到有十几位农民在考古队员的指挥下,挖掘、挑泥土。那次我们还见到正在考古现场的张敏队长,这位南京博物院的考古专家给人的感觉很干练,浑身充满活力。
说实在的,当时我很羡慕从事这样的工作。后来我虽然没有成为考古队员,却能成为一名到处跑的文化记者,现在也是一位热爱旅行的写作者。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感谢像肖兄这样的良师益友。

2006年春天,我陪我的东家《东方文化周刊》的编辑记者来高邮,当时接待我们的是宣传部副部长姜文定和其他高邮朋友。记得姜部长带我们去刚建好不久的龙虬庄遗址时,花丛中飞满白色和黄色的蝴蝶,可把我们那些美女编辑们乐坏了,她们说从来没有看过这么多的蝴蝶——谢谢蝴蝶,给了我这个高邮人多大的面子!
如此算起来,我已经有11年没有去过龙虬庄,哪怕就是为了看蝴蝶也要去,对吧?
阔别11年的“龙虬庄遗址”,比以前更有气势,穿过那个古朴粗犷的门,四周静悄悄的。花草树木都以它们各有姿态生长着,只有远处斑鸠的叫唤声,眼前的气息让我特别熟悉——借用那句广告词:就是这个味道。
其实,故乡的味道是说不清的,那种干草气息会一直深藏在你的记忆里,不会因为光阴流逝而改变。其实,从大路边的“人字形”门头,到龙虬庄大门并不远,我是有意放慢脚步去阅读这些久违的故乡风景。

龙虬庄遗址卖票的是一位姓倪的老先生,我去高邮其他文化遗址都是买票的,道理很简单,作为一位身在他乡的高邮人,也算是为家乡文化事业添砖加瓦吧!
进门一眼就看见草地上那座龙虬先人“男猎女织”的雕塑,在他们的上空是各种姿态的大树,上午的阳光投射下来,在草地上形成斑驳的光影,让人恍惚。
龙虬庄遗址的核心精华部分是那座茅草屋顶的遗址博物馆,再向后有龙虬庄考古原遗址,其他还有生活、狩猎、捕鱼、农耕、手工等区域。遗址周围都是静静的河流,经考证这条河就是7000年前的“护庄河”。

博物馆里布置很精致,可看到挖掘出来的蚌壳、鹿角、兽骨以及先民们制造的工具、陶罐等,从这些当中可发现龙虬先民们心灵手巧,手工技艺水平非常高。他们会狩猎、捕鱼、种植、会做工具做陶器,还会烧菜,会自娱自乐。
据说7000年前,海水从江淮地区退去,海岸线东移。这里慢慢形成森林、湖泊、沼泽地,这支先民来到这里定居,开始了漫长的农业耕作,打鱼狩猎的生活。
龙虬庄遗址当时是母系社会,女人当家,男人打鱼狩猎,当时男性身高170com左右,男人女人平均寿命只有30岁左右,40岁就是高寿了。可以想象,当时龙虬庄部落都是青壮年居多,没有老年化现象。

那天,我认真拍摄那些7000年前的遗存,比如用于狩猎的骨镞、骨凿,用于生产的石锄、石刀;比如制作的陶器,不但有灰陶、红陶和黑陶之分,有些陶器上还有手绘的图案。尤其是那些与茶壶大小的陶器,不就是像宜兴的供春壶嘛!还有那些可爱的小陶猪,很有现代造型艺术的感觉。此外,他们还会用动物的骨头做骨哨,也就是我们现在笛子的前身。
人类历史是镜子,龙虬祖先更是镜子。如今高邮被评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这片土地呈现的文化、艺术、民歌等现象,我相信多少是有基因遗传的!

龙虬庄文化遗址最有价值的是,挖掘发现了7000-5000年之间的碳化稻米,将我国人工栽培水稻的历史提早到5500年前。更让人兴奋的是,龙虬庄文化遗址首次出土一种“陶文”的象形符号,比甲骨文提前了上千年,太了不起了,有专家学者把“陶文”的发现誉为中华文明的一束曙光,真是恰如其分。
龙虬庄遗址的发现,我们要特别感谢一个人,就是已故考古专家张正祥先生。
上世纪70年代,南京博物院的考古专家张正祥先生,全家下放在当时高邮县一沟公社红胜大队(即龙虬庄)。1970年2月28日,春雨刚停,张正祥先生和一位邮递员大叔在渠边行走时,他出于职业的敏感,在挖鱼塘的断层泥土里,发现大量的丽蚌壳、鹿角、兽骨和陶片,让这位有着多年考古经验的人,认定这里6000年前有人居住过。后来经过张先生等人以及高邮文化部门积极呼吁,终于引起国内各方面的重视。
1993年4月到1996年4月,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等单位组成联合考古队,经过4次对龙虬庄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共发掘出新石器时代的各种器皿、骨头化石上千件,发现居址4处、墓葬402座,出土各类文化遗物2000多件。这项考古震惊了考古学术界,引起海内外的广泛关注。
不过,最早发现龙虬庄遗址的张正祥先生,2005年患病不幸逝世。某种程度上,这位南京下放干部似乎就是上天派来的发现者。如今来高邮龙虬庄遗址旅游的人,要记住像张先生这样的文物保护者。
干部下放是历史上“政治运动”的产物,但凡事都是双刃剑。在我们高邮历史上,上世纪50年代,一批中央文化部下放干部就在高邮推广过“新民歌运动”,让高邮后来出现许多民歌整理者、演唱者和推广者。同样,在上世纪60、70年代一批南京等地下放干部对高邮的文化、教育、艺术等方面也有过不可磨灭的贡献。
上世纪70年代,我曾有过几年高邮某乡镇的生活,有幸接触到许多南京下放干部,也有一批与我同龄的知青朋友。在我的印象里,那些南京下放干部中,许多人多才多艺,会写文章,会唱美声,会朗诵,会吹箫,在一些大会上表演文艺节目也十分拿魂。
至今我还记得,一次夏季纳凉,我听到一位南京下放干部唱了《松花江上》,那苍凉激昂的男中音让人久久挥之不去。我还在一个冬夜里,听一位下放干部(印尼华侨)在家里吹箫,萧声如泣如诉,感人至深。我还认识一对南京下放干部夫妻,先生姓归,妻子姓陈,他们都是演员,夫妻俩都非常漂亮,记得夫妻俩一起出现在小镇上,就像一幅画。
在我的生命中,一路过来有许多这样的优秀的人。如今都失去联系,天各一方。也许他们当时的呈现都是不经意的,却为我的青少年时代,提供了一种人生样本。一个人只有向往高贵,向往美好,才会有追求和向往的动力。这种潜意识的东西是无形的,也看不见,就像播下的种子,总有一天会开花结果。
这次在高邮,我有幸和曾经在那个小镇生活过的老友们吃饭,席间的朋友大都是在南京、上海、扬州、高邮等地的准成功人士。我当时讲述了这种“独特现象”时,朋友们都深以为然!
记得那天上午从博物馆出来,我还到后面园子里转了一圈,看了以前的发掘现场(我甚至有些自豪,当年我曾来过)。在生活、狩猎、手工等区域,有许多龙虬先人的雕塑,让人有置身在龙虬部落的感觉。他们的房子也有像吊脚楼——干栏式的建筑,也有像后来的草房。尤其是见到那些草房里的纺车、农具以及烧草用的“锅箱子”,很是亲切,觉得7000年并不遥远。
不过,非常惋惜的是,大约在5000前左右,由于海面的上涨,低洼的江淮平原又成了汪洋一片,也给龙虬庄遗址先民带来大灾难,他们的再次迁徙,象征着生活了2000年的文明消失在大水之中。
龙虬庄的先民究竟迁徙到哪里,至今是一个千古之谜。据姜文定先生《漫步高邮》一书所说:据有关专家分析,一种可能是向西,迁徙到淮河上游一带;另一种可能是,先向北到达山东,后向东到达日本九州北部,成为日本弥生文化的重要来源之一。
1996年,日本金泽大学教授中村慎一先生一行十几人来高邮龙虬庄考察,他很激动地指出:“龙虬庄的稻作,是日本弥生文化的母亲!”其实,这句话不是空穴来风,日本研究者发现,除弥生文化早期遗址的粳型稻与龙虬庄遗址相同之外,所饲养的家猪、家犬,渔猎手法,制作工具等都与龙虬庄遗址相同,比如龙虬庄文化中常见的镞、镖、凿、锥、箸、针等,都可以在弥生文化遗址中见到,连大小都相仿。还有弥生文化中的陶器以及常见的装饰品都可以在龙虬庄遗址文化中找到影子。
这就为日本历史上突然出现在九州北部的弥生文化,找到了一个合理的解释。当然,这只是一家之言。
不管怎么说,在我的家乡高邮,能有这样一个7000年前人类文化遗址,足以让我们这些后人为之骄傲!
标签: 考古遗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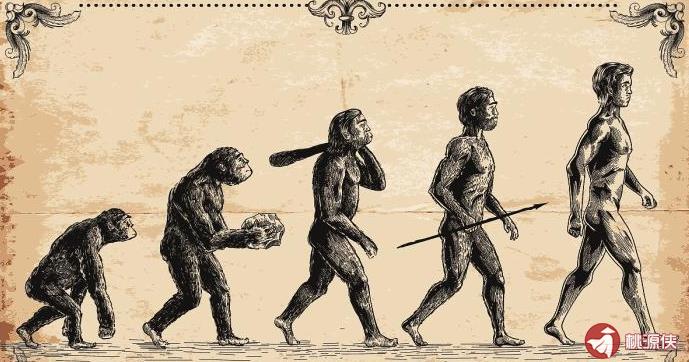

还木有评论哦,快来抢沙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