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郭伟民研究员为 “走进长江文明之大溪文化主题展” 所作。本号经作者同意转发。因篇幅所限省略了注释,若有参考或引用,务请查阅原文。
前言
大溪文化发现至今,学术界对它的认识在不断变化和深化,这一认知过程与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有密切关系。大溪文化发现与研究大体经历了二个阶段,自1960年代被命名至1980年代为第一阶段,在这个阶段,搭建以文化历史为研究取向的时空框架成为中国考古学的主要使命,大溪文化也不例外。围绕大溪文化的类型与分期、与其他文化的关系,学术界做了大量的田野和室内工作。这一工作的成果是大致建立了大溪文化的时空架构,这项工作至今也还未结束。改革开放的中国考古学,在技术、方法、理论等方面获得了飞速发展。进入1990年代,由于对考古学文化认知的差异,学术界仍然在为确立考古学文化的标准争论不休,进而对大溪文化内涵和外延的界定莫衷一是的时候,国外新的考古学思潮大量引进,过程考古学与后过程考古学同时被介绍到中国,因而回答过去的事件如何发生以及为何发生成为新的研究取向。于是,人们尝试从不同视角、运用不同方法来研究大溪文化,比如文化系统与结构、生态环境、聚落形态、社会组织与形态、经济技术等方面成为了解大溪文化的变化过程以及解释这种过程的原因的新内容。显然,这些内容的背后具有过程主义和后过程主义的思维取向。
1990年代以后,大溪文化的研究进入了第二阶段。其主要特点是:一方面完善文化序列,并继续就该文化的一些基本概念开展探讨;另一方面出现的新变化是不再纠缠于文化性质的界定,而是将重点投向建立了解人类过去的理论、方法和技术模式上来。比如对于石家河聚落群的考古调查与研究;阴湘城的考古调查与发掘;城头山聚落的考古发掘;澧阳平原的聚落形态与环境考古研究等等,继而从传统的谱系研究转向社会组织、人地关系、经济技术等方面来认识人类的过去。在这样的研究层面上,大溪文化——这个过去单纯以陶器来界定的文化——的内容一下子变得丰富多彩起来。
大家逐渐认识到,那种单纯以陶器来作为界定文化的唯一标准显然存在重大缺陷,考古学文化至少应该包含了一组或多组反复共存的遗物、遗迹,只有当这些因素相互关联和共存在一起并多次出现时,才能对一个特定的考古学文化作出正确认知。诚如严文明先生所强调的那样:应该将聚落形态、墓葬形制、生产工具与武器、生活用具、装饰品(包括艺术品和宗教用品)等综合起来作为识别和界定每个考古学文化的依据。当然,反复共存的组合存在的时间、空间的尺度如何把握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人们的主观认知差异极大,这也正是考古学文化研究存在的严重问题。真实的客观世界时刻在发生变化,我们却以静止的观点去看待世界,必然导致对考古学文化产生重大的认知差异。因此,围绕大溪文化诸遗存的性质和命名就是一个生动的例证。不过,正当考古学文化命名问题需要正本清源的时候,中国和世界考古学的进程已经走得很远了。
湖南大溪文化的考古与研究,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几十年来中国考古学的变革历程。 它既是长江流域考古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的进程,也与新中国考古工作和学术研究的进程密切相关。下面分几个方面阐述。
壹、湖南大溪文化的考古发现
湖南大溪文化的田野工作,首先是从湖南新石器时代考古遗址发掘开始的。1955年7月长沙县五区龙头铺(现为株洲市龙头铺镇)烟敦冲遗址的试掘可以作为开始的标志。1967年4—6月,湖南省博物馆对澧县梦溪三元宫遗址进行了小规模的试掘,发表的简报对下层出土的以泥质红陶和夹砂粗陶,上层的细泥黑陶和泥质灰陶为代表的遗存的文化性质并没有作出定性的结论,但发表了彩陶的材料,该陶片为泥质褐色胎,外壁涂红衣,上绘黑褐色弦纹、菱形及圆弧形等组成的图案,发掘者认为这些图案显然具有某些大溪文化的风格。
1974年秋季,澧县梦溪三元宫遗址再次发掘。这次发掘的成果颇丰,共开探方12个,探沟4条,发掘面积共计296平方米。共发现灰坑12座,墓葬23座及大量文化遗物,在湖南省还是第一次发掘新石器时代的墓葬。发掘报告将出土遗存分为早中晚三期,认为早、中期遗存属于大溪文化,晚期属于屈家岭文化。这是湖南第一次明确提出发现大溪文化遗存。该报告还指出,三元宫遗址经历了大溪文化和屈家岭文化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这两种文化之间,不但有明确的地层叠压关系,而且从很多器形可以看出有着承袭关系。这为进一步探讨大溪文化和屈家岭文化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的资料。这是从湖南的视角最早提出的涉及大溪文化与屈家岭文化关系的观点。
1978年11月发掘安乡汤家岗遗址,发现了12座墓葬及大量遗物。这是第一次指明发现“大溪文化墓葬”。其早期的10座墓葬,特点十分突出:无墓坑,不随葬生产工具,陶器以盘、碗、釜和钵、碗、釜为常见的组合。在这些陶器中,主要以戳印、蓖点、刻划、拍印(或模印)的花纹图案为装饰。这种形式的墓葬材料,在同类型文化遗址,如四川巫山大溪、湖北枝江关庙山、湖北松滋桂花树中都不见。发掘者认为:汤家岗遗址中期墓葬与松滋桂花树、巫山大溪的比较早期的墓葬基本接近,而汤家岗遗址早期的墓葬“似比现已发现的其它大溪类型文化遗址的墓葬更早一些”。由于对这批墓葬的文化属性及年代认知的差异,遂产生了此后关于湖南大溪文化特征上的歧见与争论。
1979年冬季发掘澧县丁家岗遗址,共发掘面积300平方米。报告将所出土的新石器遗存分为三期,指出这三期具有明显的大溪文化特点,其文化内涵与汤家岗、三元宫遗址尤为接近。其第一期遗存仅在汤家岗遗址最下层和早期墓中见到,是大溪文化最早期的遗存。第二期与枝江关庙山遗址大溪文化第一期遗存出土很接近。
1980年冬,发掘安乡划城岗遗址,发掘面积200平方米。发掘出土了一批墓葬,此外还有房址、灰坑、窑址等。报告将材料分为早一期、早二期、中一期、中二期、晚期几个期别。认定早一、早二期属于大溪文化中期和晚期,中一、中二期属于屈家岭文化早期和晚期,晚期属于长江中游地区的龙山文化。
1980年代发掘的遗址还有华容车轱山、刘卜台。车轱山遗址于1982年冬发掘,发掘面积100平方米,清理了129座墓葬。报告将早一期、早二期遗存及第一期墓葬划为大溪文化,而将与之处于同一个墓地且器物形态、组合均极为相似的第二期墓葬与三、四期墓葬一同划为屈家岭文化。刘卜台遗址于1986年初发掘,发掘面积75平方米,出土了一批遗物和房址、灰坑、灶等遗迹。报告将材料分为三期,认为一至三期都是大溪文化的范畴。
1990年代,湖南对于大溪文化的考古发掘主要是连续多年的城头山遗址发掘。城头山的考古发掘自1991年开始,这一年,考古发掘的目的是解剖城墙以确定该城的年代,考古出土的资料为7组,认为第1组为大溪文化,第2—5组为屈家岭文化,第6—7组为石家河文化。其清理出的层位关系表明城墙的建造年代为屈家岭文化早期晚段。此后,连续开展工作十多年,发掘面积达6064平方米,并于1996—1998年连续对西南城墙和东城墙加以解剖,得出清楚的层位关系,并最终确定城墙的筑造年代为大溪文化一期,超过距今6000年。城头山连续多年的工作不仅确定了大溪文化古城,还获得了大量的大溪文化时期的遗存,除了城墙、城壕,还有水稻田、祭坛、祭祀坑、墓地和墓葬、建筑、窑场等一系列重要遗迹和丰富的遗物,为湖南大溪文化的研究提供了极为重要的资料。1990年代相关大溪文化遗存的发掘还有丁家岗遗址第二次考古发掘、汤家岗第二次发掘、划城岗遗址的第二次发掘。这些遗址的发掘补充了大量的资料,丰富了相关的遗存和遗物。
2000年以来,针对大溪文化遗存的发掘,开展得并不多,但是有几次发掘仍然非常重要。汤家岗的第三次发掘于2007年度进行,发掘面积355平方米,不仅发现了一批大溪文化遗迹,还首次确认了汤家岗文化时期的壕沟及其他重要遗迹。优周岗遗址的发掘属于二广高速公路抢救性考古发掘项目,于2009年冬季开始,至2010年冬,共完成发掘面积3000余平米,除发现一大批石家河文化、屈家岭文化和大溪文化遗存以及少量汤家岗文化遗存外,最重要的是发现了一系列属于大溪文化与原始宗教类活动相关的遗存,包括祭坛、兽骨坑等相关迹象。
2000年以来,城头山遗址的考古发掘也时有进行,2011年护城河发掘,同年为配合文物保护工程设施建设发掘358平方米,揭示出东部大溪文化城墙的建造过程。2012年春配合西南城墙保护展示,发掘218平方米,揭示出从大溪文化早期至石家河文化时期的多组建筑遗迹。2014年,首先发掘了城址西南护城河外庙坟上的一处台地,发掘面积375平方米。确认该台地为新石器时代人工修建而成的一大型台基,其始建年代不早于城头山大溪文化四期,废弃年代不晚于石家河文化时期。依堆积特征,其修建时代很可能与城头山屈家岭文化时期城墙与护城河的修建同时。另外,在庙坟上台地底部,发现早至大溪文化二期的系列柱洞与灰坑遗迹。稍后,在城头山遗址南部现存护城河内岸,城墙豁口之外,东西向布设5×5平方米探方四个,在南北向横跨地表现存护城河布设5×5平方米探方七个,实际总发掘面积216平方米,发现了大溪文化时期遗存。
贰、湖南大溪文化研究
湖南大溪文化的研究,有一个渐进的过程,这个过程从总的方面来看,最初是对文化内涵的了解,进而对文化性质的认定,再发展到文化分期、文化关系的研究层面。1970年代,学术界还处在积累资料的阶段,对于大溪文化的认识,也仅仅局限于考古报告中最末部分的总结中,相关综合的研究还很少,甚至还没有单独讨论大溪文化的专题文章。就两湖地区而言,相关遗址的发掘时间和报告发表时间并不一致,因而无法了解1970年代对大溪文化研究的完整过程。
1970年代较早发掘的几个遗址中,松滋桂花树是1974年12月—1975年1月发掘,1976年发表考古报告。江陵毛家山遗址是1975年5月发掘,1977年发表考古报告。巫山大溪遗址第三次发掘是1975年10月至次年1月,1981年发表考古报告。桂花树的考古虽然还略显粗糙,但发表了大量器物,多数器物是采集所得。通过这次田野工作,认识到“无论从遗址或墓葬的文化遗存来看,都与四川巫山大溪遗址的文化面貌有许多相似之处,其中尤以陶器的风格更为接近。大溪文化特有的仰身屈肢葬在桂花树也有发现。桂花树遗址有一定数量的陶瓶,则是大溪文化中所没有的,而湖南澧县梦溪遗址却有同样类型的器物。因此,我们认为,桂花树早期文化遗存与大溪文化面貌基本一致。结合江陵毛家山遗址大溪文化的试掘资料,可以看出,大溪文化的分布范围到达长江中游,南近洞庭湖滨,其东限已达江陵。”桂花树的报告首次将大溪、桂花树、梦溪冯家巷(三元宫)遗址所出遗物列为同一性质的文化——大溪文化遗存,意味着大溪文化的分布范围扩大到了洞庭湖畔。至此,在学术界将大溪文化的分布范围圈定在了川东和两湖平原的大部分地区。
湖南地区的大溪文化,从这时开始正式成为学界关注的课题。固然,湖南地区大溪文化,离不开对大溪文化内涵的探讨和分析,与其他区域的大溪文化遗存相继发现这一大背景是相关联的。
何介钧最先对到大溪文化进行综合研究,1980年11月在湖北武汉召开的中国考古学会第二次年会上,何介钧提交了《试论大溪文化》的论文,明确提出大溪文化的分布范围西道四川巫山,东到鄂东黄岗,北到湖北江陵或许更北的京山,南到洞庭湖的北岸。它跨越了大江南北,东西一千多里,而中心地区当在江汉平原西南部和洞庭湖北岸。该文首次对两岸三地的大溪文化做了系统考察和全面归纳,总结了大溪文化的基本特征和文化内涵。并对大溪文化进行了分期。他的分期的第一期,以汤家岗早期墓葬、下层地层、丁家岗遗址下层及同层的墓葬为代表;第二期以关庙山第六、七层、蔡台第五层、丁家岗遗址上层和三元宫下层为代表;第三期以毛家山遗址、关庙山遗址第四、五层、红花套遗址一、二期文化遗存、三元宫中层为代表;第四期以大溪墓地、桂花树遗址大溪文化层、红花套遗址第三期遗存为代表。
与何介钧不同看法的观点也在这个会议上提了出来,林向即认为湖南三元宫遗址的一些“与大溪文化相同的文化因素”的遗存,不宜称为大溪文化。他指出:湖南澧县三元宫遗址的早、中期确有许多与大溪文化相同的文化因素,如外红内黑夹砂陶、发达的圈足器、伞纽器盖、空心陶球等。可是不容讳言,有着很大的差异,如三元宫没有大溪文化的典型器物群:巨形斧、圭形凿(晚期才有)、曲腹杯、筒形瓶、玉璜、玉玦等,而三元宫有火候很高的红胎或灰胎黑皮陶,为大溪文化所不见。三元宫的折壁碗、敛口折腹豆、大口尊、无底豆式器座,中期的彩陶纹样,两面有凹槽的石斧,都与大溪文化异趣。因此,他认为,三元宫遗址的早、中期可能只是受大溪文化强烈影响的另一种原始文化,也不同于屈家岭文化。所以,大溪文化在湖南的分布大概要另外去找。
1982年,张之恒发表《试论大溪文化》,该文将大溪文化分为五期,他认为大溪文化分布地域东到汉水、西达川东、南至湘北、北至荆州北部。也就是说,承认三元宫、王家岗墓葬为大溪文化;但汉水以东不是大溪文化分布范围。
1983年,向绪成《从关庙山遗址看大溪文化分期》一文发表,该文将关庙山大溪文化遗存分为四期,并以这四期作为标尺去量其他遗址,并认为三元宫遗址早期与关庙山第一期相当;中期相当于关庙山第二期,有少量器物可以晚到第三期;晚一期略晚于关庙山第四期。冯家巷遗址中期相当于关庙山第三期前段,晚期略晚于关庙山第四期。汤家岗遗址早期相当于关庙山第一期,中期和晚期相当于关庙山第二期。对于丁家岗遗址,他认为第一、二期遗存没有超出关庙山第一期的范围,第三期与关庙山第二期相当。晚期墓葬(M1)属于大溪文化晚期。安乡划城岗遗址早一期相当于关庙山第二期,早二期相当于关庙山第三期,中一期略晚于关庙山第四期。
1984年王杰发表《对大溪文化中几个问题的探讨》,该文将大溪文化分为四期,认为大溪文化第一期至第四期有以下一些代表性的遗址:第一期有关庙山一期、大溪遗址下层、红花套一期部分。第二期有关庙山二期、红花套一期部分、大溪遗址部分、蔡台五层、桂花树墓葬部分、毛家山部分。第三期有关庙山三期、红花套二期、大溪墓葬部分、毛家山、桂花树大溪文化墓葬。第四期有关庙山四期、红花套三期、大溪遗址墓葬部分、桂花树大溪文化墓葬。并认为第四期的“文化面貌有所变化,灰、黑陶比例大增,似有向其他文化逐渐转化的迹象。”关于湖南地区“大溪文化”,该文首先从陶质陶色和器物形态上认定以丁家岗、汤家岗早期为代表的遗存的年代要相当于或晚于关庙山遗址二期,与关庙山遗址大溪文化第三期接近。另外,汤家岗遗址早期地层中出土的一些陶器,如釜、钵、盆和圈足盘在关庙山遗址第二期才开始出现,由此也可以认定,汤家岗遗址早期只能相当于关庙山遗址第二期。该文还认为湖南地区的大溪文化,虽然有大溪文化的某些特征和相似的器物,但是有更多的陶器形制和特点与大溪文化不同或在大溪文化中根本不见的,因此,把它作为大溪文化的另一个类型较为恰当。后来,他又认为湖南大溪文化和大溪文化在许多主要遗物方面区别甚大,不是用一个文化中两个类型所能解释得通的。有必要将湖南地区的大溪文化另立一名称为妥,并建议将湖南地区的大溪文化暂称为湖南大溪文化或另改名为汤家岗文化。
1986年发表了两篇重要的文章,分别是李文杰的《大溪文化的类型与分期》与何介钧的《洞庭湖区新石器时代文化》。关于大溪文化的分期,何介钧的观点与以前没有变化。李文杰的文章认为湖南地区的大溪文化与以关庙山为代表的大溪文化存在类型上的差别,可以归为大溪文化汤家岗类型,至于分期,其看法与王杰一致,认为汤家岗早期相当于关庙山二期。但他观察到了丁家岗第二期墓葬出土了折壁碗,这种碗的形态见于关庙山第一期,不过他据与二期墓葬折壁碗共存的凹沿罐认为,凹沿罐在关庙山为第二期,因此这种折壁碗也早不到关庙山第一期。
上述观点大概是1990年代以前的几种主流看法,涉及到湖南地区大溪文化的年代与特征,实际上主要是年代与分期的对应和文化性质问题。此后,也有文章对此论及,但大体没有逾越前述相关观点。如孟华平认为“大溪文化汤家岗类型”有自己的地域传统,汤家岗类型具有独特的文化内涵,有自身独具特征的典型器物组合,很难把汤家岗类型归人大溪文化的系统中。而裴安平则认为湘北洞庭湖新石器文化序列应该基于其本来面貌重新划分考古学文化,他将何介钧《洞庭湖区新石器时代文化》一文所涵盖的大溪文化分解成汤家岗文化—丁家岗文化—划城岗文化。
进入1990年代以后,一系列新的考古发现为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许多新的资料。首先是澧县城头山的发掘,以及划城岗和汤家岗遗址的再次发掘,不仅再一次证明何介钧在湖南大溪文化分期上的正确,也为一支新的考古学文化——汤家岗文化的正式确立奠定了基础。实际上,何介钧早在1980年《试论大溪文化》一文中就已明白地就丁家岗遗址下层和汤家岗下层一类遗存作了阐述,指出“它具有了大溪文化的某些共同因素,有理由认为它是大溪文化的一个发展阶段,也就是目前所见大溪文化的最早期。但大溪文化的一些特征性因素,有好些在这类遗存中尚未具备,因而又有可能认作是与大溪文化有别,比大溪文化更早的一类原始文化遗存。由于发现还不多,材料不够丰富,可以暂不另外命名,不过它对探索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是一个十分值得珍视的启示和线索。”时隔15年之后,何介钧在《长江中游原始文化再论》中指出:“当时,大溪文化的分期研究刚刚起步,这样的论逻应该是具有一定的预见性和超前意识。现在,当然可以讲得更明确,汤家岗遗址早期连同丁家岗遗址的第一期遗存比大溪文化更早,应是一种新的考古学文化,有人建议正式定名为汤家岗文化,我认为是合适的”。并强调“所谓大溪文化三元宫(或称汤家岗)类型不包括汤家岗遗址的早期,而现在提出的汤家岗文化也不是指大溪文化三元宫(或称汤家岗)类型。在进行比较研究时,必须将二者严格加以区别和限定。”正式提出汤家岗文化。
本人曾经有感于学界对所谓大溪文化汤家岗类型或汤家岗文化的概念容易混淆,提出了“汤家岗一期文化”的命名。我在《洞庭湖区大溪文化研究》一文中指出,洞庭湖区以汤家岗一期为代表的一类遗存早于大溪文化,在文化性质上与洞庭湖区大溪文化有着质的区别,应该从大溪文化中独立出来。汤家岗一期文化的提出有六个大的前提:第一,多年的工作已确认丁家岗第一期、汤家岗第一期、刘卜台第一期等遗存早于关庙山一期;第二,类型学研究的结果已经从这些遗存中提取出典型器物形态和器物组合,并显示出与洞庭湖区大溪文化遗存有质的区别;第三,一大批与之类似的遗址的相继发现与发;第四,考古工作使得洞庭湖区新石器文化序列已渐趋明朗化;第五,汤家岗遗址经过两次发掘,特别是第二次发掘为汤家岗一期文化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材料;第六,鉴于“汤家岗文化”已成为某些研究者印象中的“湖南大溪文化”,为避此嫌疑,故以汤家岗一期文化予以命名。进而指出:比较确切属于汤家岗一期文化的主要遗存有汤家岗早期地层与墓葬、即1982年报告中发表的各探方第(三)层及11座墓葬,1990年发掘的与原报告早期相当和更早的地层和墓葬;丁家岗遗址各探方第(三)层及三座墓葬;刘卜台遗址第一期的地层与墓葬。汤家岗一期文化以泥质陶为主,泥质陶又以粗泥红陶和褐胎黑皮陶为大宗,有一定数量的细砂白陶和夹砂红陶,陶器纹饰极富特点,表现为以刻划、戳印、压印、拍印作为主体。戳印纹多以一系列单组或复合纹的连弧、菱形、锯齿、水波、拆角、羽状、圆圈等纹饰为代表,间或衬以锥刺纹,压印纹主要有弦纹、蓖点纹,拍印多绳纹,陶器纹饰繁褥,造型奇特,反映了该文化独有的特质。主要的器物组合有釜、碗、盘、钵、罐、器盖、器座等。而洞庭湖区大溪文化也可以分为四期,这四期完全可以与关庙山遗址分期相对应。
1990年以后的考古发掘,城头山和汤家岗、划城岗等遗址有了明确的遗址分期和文化分期。同时,在峡江地区也陆续发掘柳林溪、杨家湾、伍相庙、龚家大沟、孙家河一类遗址,提出了柳林溪文化的命名。遂使大溪文化的性质、类型与分期问题得到了彻底解决。
湖南地区大溪文化之源解决之后,还有一个流的问题,即大溪文化的后续文化。这个问题涉及到大溪文化与屈家岭文化关系的讨论,也一度是学术界的争论的焦点。屈家岭遗址的发掘较早,屈家岭文化的提出也早于大溪文化。因此,大溪文化一经提出,就涉及到其与屈家岭文化的关系问题。1959年巫山大溪遗址发掘以后,发掘者就认为该遗存与江汉地区的屈家岭文化有区别,可能比屈家岭文化略晚一些。从学术角度而言,最先对大溪文化与屈家岭文化关系进行讨论的是毛家山遗址发掘之后。江陵毛家山的报告结尾部分就大溪文化与屈家岭文化的关系发表了意见。报告指出,毛家山遗址新石器文化遗存的性质可以归入大溪文化类型。从大溪文化的分布范围来看,它不仅仅分布在川东和三峡地区,还分布到了湖北中部的江汉平原,这与屈家岭文化的分布范围在很大面积上是重合的。关于这两个文化的关系,报告认为,从地层上,大溪文化地层被屈家岭文化地层所叠压;从文化特征上看,屈家岭文化“许多特征明显地与大溪文化相似,这些共同或相似的因素自然不能用相互影响来解释,而只能是屈家岭文化继承大溪文化(包括毛家山在内)的结果。”同时,报告指出所谓的屈家岭文化实际上包括了早期和晚期遗存,大溪文化与屈家岭文化的关系实际上是大溪文化与屈家岭文化晚期遗存的关系,即大溪文化早于屈家岭文化晚期。至于以武昌洪山放鹰台和京山慧亭水库为代表的屈家岭文化早期遗存,报告认为它是与大溪文化不同的一个文化类型,年代接近或晚于大溪文化。
1980年代,有关这两个文化的关系问题讨论热烈,主要可归结为“平行论”和“继承论”两派观点。平行论认为屈家岭文化另有渊源,它的早期与大溪文化晚期有过一段时间平行发展,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强大而最终取代了大溪文化;继承论认为屈家岭文化源自大溪文化内部,是大溪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平行论方面,王劲较早对此进行综合研究,她认为,大溪文化与屈家岭文化两个原始文化的关系,可能是互相影响的关系,而不是一前一后的发展关系。它们的起源地不同,大溪文化起源于川东鄂西一带,屈家岭文化起源于江汉平原;它们起源的时间大溪文化要早于屈家岭文化。鄂西大溪文化遗存中发现的屈家岭文化因素是文化因素影响的结果,虽然这里的大溪文化晚期有不少屈家岭文化因素的成分,但整体上来看仍然是大溪文化的范畴,这里找不到大溪文化向屈家岭文化发展的发展序列。另外,从文化交界处如毛家山遗址的出土情况来看,这里的大溪文化已经受到屈家岭文化因素的明显渗透,应为接触地带相互影响的反映。之后不久,张之恒也表述了相同的观点,认为屈家岭文化非继承大溪文化而来。主要依据是:鄂西的大溪文化之上,叠压的都是屈家岭文化晚期的遗存,还没有发现屈家岭文化早期叠压在大溪文化地层之上。鄂西大溪文化晚期,受到了屈家岭文化早期的影响,也就是说,鄂西大溪文化晚期是和屈家岭文化早期平行的。王杰也认为,从鄂西、湘北的材料来看,都是屈家岭文化晚期叠压在大溪文化晚期地层之上,还未见屈家岭文化早期叠压在大溪文化晚期地层之上。大溪文化与屈家岭文化在某个时期有过一段时间的共存,二者与互相影响的关系,目前还看不到有继承关系。进入1990年代以后,这一观点也继续存在,孟华平认为,鄂西大溪文化的一些器物很难在峡区找到直接来源,可能与屈家岭文化早期向外扩张有关。屈家岭文化早期以鼎为特征,其渊源主要在汉水下游,与大溪文化谱系不同。林邦存认为屈家岭文化是由边畈文化发展而来,边畈文化比仰韶文化和大溪文化在江汉地区的任何一个类型都更早发展为以黑陶系为主的屈家岭文化。孟华平在其论著中,将长江中游新石器文化归为南北二元系统,一个是以彭头山文化、皂市下层文化、城背溪文化、汤家岗文化、大溪文化为代表的釜文化系统,分布在洞庭湖及峡江地区,可称为南方系统;另一个是以边畈文化、油子岭文化、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为代表的鼎文化系统,可称为北方系统。在发展过程中,南北两系统的考古学文化有着不同程度的交往和影响。约距今5000年前后,这种以二元为主体的谱系结构被打破,北方系统的屈家岭文化逐步向西南发展,基本取代了南方系统,实现了空前的统一和繁荣。
另一派观点即继承论认为,屈家岭文化由大溪文化发展而来。李文杰最先表述这种观点,他认为大溪文化和屈家岭文化是先后相继的考古学文化,并以陶器形态如圈足器、曲腹杯、朱绘黑陶、蛋壳彩陶、篦点纹陶球以及石器、稻作农业、墓葬葬式等方面推断该两个文化是先后相承接的文化。何介钧认为屈家岭文化早期和大溪文化晚期非常相似,而这些相似的特点在大溪文化的更早阶段即可以找到其原始形态和萌芽状态。因此屈家岭文化早期的大量特点和器物可以从大溪文化整个的发展趋势中找到其演变轨迹。向绪成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只不过他与李文杰、何介钧在大溪文化分期上认知不同,他将以屈家岭早期、武昌放鹰台、京山朱家嘴、王家岗上层墓葬、度家岗墓葬、划城岗中一期墓葬为代表的遗存列为大溪文化第五期,认为这与大溪文化第四期性质相同。持此类观点的还有张绪球,认为划城岗中一期墓葬、三元宫晚期墓葬、丁家岗晚期M1、车轱山二期墓葬、王家岗墓葬等遗存应该划为大溪文化第五期。
上述两派观点分歧不仅涉及到如何认识长江中游新石器文化的谱系结构和文化进程,也涉及到如何认识考古学文化面貌、性质的标准问题。具体到矛盾焦点上,在于如何认识大溪文化晚期与屈家岭文化早期一批遗存的性质问题。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两派观点还有着明显的交锋。如对于屈家岭遗址下层遗存文化性质的认识上,向绪成认为,类似于屈家岭下层的黑陶遗存,无论是江汉平原(汉东)还是鄂西、湘北,在文化性质上是一致的,应该是同一文化,黑陶遗存很多器物是可以在大溪文化一至三期中找到原来的形态的,如豆、曲腹杯、细颈壶、瓶等,而在典型屈家岭文化中,这些器物基本不再存在,而典型屈家岭文化的器物,也不见于黑陶遗存中,这就意味着黑陶遗存基本与大溪文化的面貌一致,属于大溪文化传统。朱乃诚列举了屈家岭遗址一至第三次发掘的最早一批遗物,也就是第一期遗存,与鄂西湘北大溪文化进行对比,发现有几乎大多数器物都高度一致,进而推断屈家岭遗址下层就是大溪文化。屈家岭遗址第三次发掘资料,则证实了汉水以东地区的屈家岭文化也是由大溪文化演变发展而来的。王杰则不同意,他认为,屈家岭遗址下层与大溪文化晚期在遗物的形态、纹饰、陶色等方面显著不同,是两个文化面貌根本不同的遗存。
实际上,对于大溪文化与屈家岭文化关系的讨论,主要集中在相当于关庙山大溪文化四期或四、五期及其同类遗存的认知上,这类遗存大致晚于大溪文化三期以后,在鄂西峡江及洞庭湖区等地出现了黑灰陶逐渐取代红陶的过程。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本人在城头山整理期间,确实发现了大溪文化三期以后的一些现象,即无论从聚落形态还是陶器形态都发生了重要变化,这些变化也确实不好理解。随着汉东地区包括油子岭、龙嘴及谭家岭遗址的发掘和材料的刊布,问题的答案才渐渐明朗起来。并接受了屈家岭文化起于汉东的说法,同时对屈家岭文化之前所谓大溪文化四期及其相关遗存进行了考察。并指出,以城头山大溪文化第四期为代表的一类遗存,在陶质陶色、器物组合与形态上,均与大溪文化有明显的差异。因此,有必要将这类遗存从大溪文化中甄别出来,可以考虑以油子岭文化命名。
这桩学术公案,到目前为止大致已经尘埃落定,即屈家岭文化的渊源不在大溪文化内部,而是源自汉东地区的油子岭文化。在屈家岭文化取代大溪文化之前,油子岭文化已经取代了大溪文化并完成了长江中游新石器文化的整合。
湖南地区的大溪文化的整体性研究多有成果面世,何介钧在1980年代的文章中对湖南大溪文化的分期及各期的相关特征进行了全面研究,1990年代也发表了相关论著对此专门加以讨论。本人对于湖南大溪文化研究也多有涉及到文化分期、文化关系及相关问题的考察。从文化传统上,大溪文化是两湖峡江地区承上启下的一支重要考古学文化,它第一次对两岸三地的史前文化进行了全面整合,它从距今6300——5500年大约有八百年的发展演变史,它在发展过程中,区域内部交流频繁,与外部文化也发生过密切交往,它的重心在长江中游的西南部。后来,江汉平原东部即大洪山南麓汉水以东地区获得快速发展,催生出一支全新的考古学文化——油子岭文化,该文化后来全面取代了大溪文化,实现了长江中游文化的空前统一。
叁、湖南大溪文化时期的经济与社会
大溪文化是一个具有多种经济形态的社会,不同地区因地制宜地发展自己的生业经济,湖南大溪文化所依赖的环境在湖南地区主要表现为平原景观,当时洞庭湖平原河网交织,很多大溪文化的遗址就在河流附近的小岗地上,有的邻近湖沼。当时的气候正处于全新世大暖期阶段,整体温度还略高于现在,这样的环境和气候对于稻作农业来说是得天独厚的。澧阳平原是稻作农业较早出现的区域,这里从距今8000年以前的彭头山文化阶段就开始了早期稻作农业,从相关出土水稻遗存分析,从彭头山文化,经皂市下层文化、汤家岗文化,到大溪文化,水稻的性状由野生稻向栽培稻迅速进化,人类对于水稻的认知促进了稻作农业的发达。汤家岗文化时期在城头山遗址发现了水稻田,这种水稻田的形状及相关配套设施均呈现出完善的稻作农业水平,大溪文化时期城头山也发现了水稻田,城头山大溪文化阶段的城壕内发现了大量的水稻,说明当时稻作农业已经成为主要的生业经济。大溪文化的农业即使在当时东亚地区也是非常发达的,稻作农业对于水的利用与管理非常重要,澧阳平原从环壕聚落以来,就开始了对于水资源的利用,聚落选址在临水的岗地,这也正是稻作农业的实际需要,水稻需要水,需要水来灌溉,且能给排,这些都为水的管理提供了前提。
固然,在这样的平原水乡环境下,相关的辅助经济或许仍然很重要,城头山遗址也出土了不少动物骨骼,有獾、象、鹿、麂、牛、貉、猪等动物骨骼,其中猪骨经鉴定为家猪,说明狩猎和家猪饲养很普遍,在水生动物方面有龟、鱼、蛙,也有禽鸟的残骨。这些动物或都进入当时人们的食物领域,表明当时以稻作农业经济为主,并有一定的渔猎经济成分作为补充,这也是南方平原水乡地区“饭稻羹鱼”生业经济的生动体现。湖南大溪文化阶段对于植物的利用也非常充分,城头山遗址发现了丰富的植物遗存,有作为食物的薏苡、粟、茨实、慈姑、野菱,也有桃、野李、李、高粱泡、冬瓜、黄瓜、葫芦、蘡薁,还有苋、藜属植物,这些均可作为食物。大量的木本植物如各种乔木或灌木也可以成为人们生产和生活上的工具和用具。城头山还发现了原始的布,或许也是植物制成。
湖南地区大溪文化时期的经济技术,从整体上来都是在稻作农业经济的大背景下展开的,农业作为生计之需,是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因之,围绕提高稻作农业的技术也应相应发展。比如灌溉、水运水利设施等也应有所提升。同时,也应有相应的农耕工具的改进,但目前这类生产工具的发现仍然不多,城头山遗址曾经发现骨耜,也有一些石质工具如石斧、石锛的出土,但这类工具发现不多,不可能是当时人们最常见的生产工具,推测应该是以木质农具为主,这类有机物很难保存。石器不发达是洞庭湖平原史前遗址的普遍特征,或许与这里的沉积黏土环境和缺少石材有关。谈到手工业技术,大溪文化时期制陶技术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在陶土中添加掺合料已经非常普遍。因此夹炭、夹砂、夹蚌、夹草木灰、泥质、细泥等多种陶质均有体现,陶色方面也色彩纷呈,有红陶、橙黄陶、白陶、灰陶、酱陶、褐陶、红彩、黑彩、酱彩等多种着色和陶衣的技术,陶器的纹饰有绳纹、刻划、戳印、镂孔、压印、篦点、叶脉、水波等多种装饰手法,在烧制方面已经有了专门的陶窑,这个时期的陶窑有窑炉、火堂、窑床、烟囱等较为复杂的结构,这都反映了制陶技术的进步。当时一些彩陶或薄胎细腻红、黑陶器已经成为某种特定的产品,流通于聚落和社团之间。聚落之间的交流或许已经出现了早期的贸易方式,贵重物品的远距离交流也已经出现,城头山遗址所出土的玛瑙璜、玉玦、绿松石坠或许就是远程贸易而来。与此同时,大溪文化的白陶、彩陶也向外传播,遍及岭南及长江流域。这些既是与外界联系交往的证据,同时也为研究当时的贸易提供了参考。
大溪文化的社会,已经有了一定的组织方式,从建造城头山城池来看,需要动用大量的人力物力,还需要统筹规划与精心设计,人员的管理和调配都需要一定的组织才能进行。当时的社会显然已经开始出现分层,城头山城址的东部,曾发现了大溪文化时期的祭坛和墓葬,从墓葬的情况来看,已经出现了明显的社会分化,等级较高的墓葬埋葬在祭坛之上,随葬器物也较为丰富,这些高等级的墓葬成排安置,具有一定的规律,或许对应着当时的上层集团。在这批墓葬的周围,则是等级较低的墓葬,多为屈肢,基本没有随葬品。在大溪文化二期城墙的墙基,还发现了一具人骨,没有墓坑,没有随葬品,人骨似为弃置,这或许与某一类城墙奠基的行为有关。这些行为实际上也是大溪文化人们精神意识的体现。祭坛、祭祀坑、墓葬以及相应的遗存反映了当时人们的意识形态,这种行为已经从多神崇拜进入到了具有某种统一信仰和一神崇拜的范畴,具有特定身份的人充当了人神之间的使者——巫师作为掌握和传达神灵意志的介质,或是这个时代颇具风尚的精神坐标。
大溪文化出现了中国最早的城池,城头山城址的出现,犹如一道醒目的风景,将野蛮与文明划分开来。城头山城池势力范围或影响力所辐射的区域,目前还无法做出准确估计,但它的周边显然已经结成聚落共同体。它周边同时期的聚落都比较小,说明城头山城池时期已经有了一定的城乡之别。这样的规模和形态,乃是远古中国城邑形态的真实写照。所谓邦国、古国,实则是某个区域的城池和周边村社之间形成的共同体,这些共同体构成社会结构上的城邦形态,在这个意义上,血缘与地缘的结合更加紧密。城头山大溪文化史前城池的出现,拉开了中国文明化进程的序幕,由此而预示了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结语
湖南大溪文化的考古发现与研究,经过几十年、几代人的努力,除了认识其文化性质、建立文化序列、完善文化分期外,还从聚落形态的层面对其开展了大规模的考古发掘与研究,这些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目前已经对以洞庭湖澧阳平原为中心的区域大溪文化遗存和文化有了基本的揭示和掌握,田野调查和发掘也积累了大量的资料。大溪文化作为湖南新石器时代重要的文化阶段,其建立的第一个史前古城——城头山,也已经成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进入“十二”、“十三五”国家大遗址保护项目。湖南正在尝试建立环洞庭湖片区史前遗址的整体性保护体系,古老的文化正在新的历史时期焕发出新的生命活力。但是,从学术和业务角度而言,大溪文化研究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大溪文化遗址的保护与利用对于考古学家、文物保护专家、地方政府和当地民众来说,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因此,文化遗产的保护、研究与传承、利用,将任重而道远。
湖南参展的部分出土遗物

城头山遗址出土的陶擂钵

城头山遗址出土的红陶釜

城头山遗址出土的折腹红陶鼎

安乡划城岗遗址出土的灰陶甑

安乡划城岗遗址出土的高圈足白陶盘
全文完
标签: 考古遗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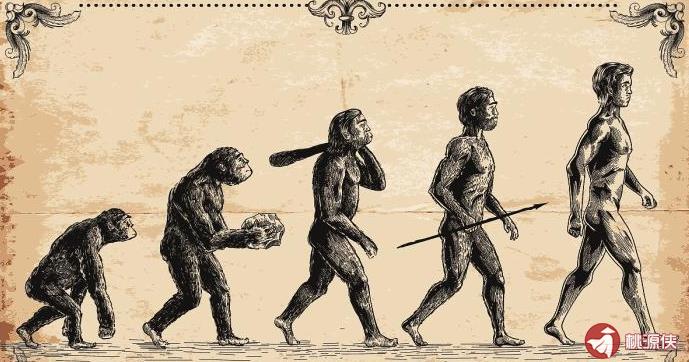

还木有评论哦,快来抢沙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