峙峪遗址发现已经50年了。然而,一个近乎伟大的遗址被遗忘在角落里太长时间,以至于“蛛网满布”、“满目疮痍”,失去了它应有的光环。之所以用这样的题目和这样的开篇,是因为一个让人喜爱、让人心疼的遗址,在研究、保护以及学术界地位等方面与其内涵差距实在太大了。

峙峪遗址现状(周围已被峙峪露天煤矿包围)
为什么这么说?让我们慢慢揭开峙峪遗址的真正面目吧!
一、生不逢时
峙峪遗址是华北地区发现的一处重要的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位于山西省大同盆地西南朔州市黑驼山东麓峙峪河与水泉沟交汇处;遗址面积南北长100米,东西宽15米。石制品丰富,动物化石密集、发现烧石和烧骨等多块,人类枕骨一块,装饰品1件、各类动物牙齿5000余枚。其地质时代属晚更新世,经C14测定,距今为28945(±1370)年和28135(±1330)年。

峙峪遗址现状,被峙峪煤矿蚕食到仅剩遗址本体,一墙之隔的峙峪煤矿被叫停后自燃现象严重
峙峪遗址发现于1963年,并进行了唯一一次考古发掘。
贾兰坡先生对峙峪遗址十分重视,专程赶来太原呆了一段时间,并将发掘材料一一过目,从中挑选了818件带回北京,准备整理发掘报告。就在此时,文化大革命的脚步已经来临,研究工作被迫停了下来。就在1963年“四清运动”开始了,紧接着就是“文化大革命”也随之而来,研究工作被迫停止下来。
贾兰坡先生在《悠长的岁月》中记录了他的这一段经历:“我能自由写作和外出调查大概是从1971年夏天开始的。我和盖培先生、尤玉柱先生等在《考古学报》1972年第一期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山西峙峪旧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在写这份报告之前,我们曾前往调查……”此时,峙峪遗址已经 “灰头土脸”地躺了九年。
二、永久定格
1971年,已经63岁的贾兰坡先生在经历了文革初期的冲击重新获得研究的自由,立刻投入了峙峪遗址的研究,并在1972年复刊的第一期《考古学报》上发表了《山西峙峪旧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这个报告从地貌地层、动物化石、文化遗物、人类化石、生活环境等各个方面对峙峪遗址进行了比较详细的研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研究者用很大的篇幅对峙峪遗址中出现的各种动物的国内外分布范围、生活习性乃至气候环境进行了详细论证,甚至应用了最少个体数的研究方式。这在之前的旧石器考古报告中十分罕见。用现在的眼观看,这些属于环境考古学研究方法。可见贾兰坡等人当时的研究化石十分超前的。
报告的另外一个亮点是提出了著名的“华北旧石器两大传统”。
峙峪遗址“石器文化”的研究可以说并非完美,甚至连好都说不上。因为发现的石器材料有15000多件(尤玉柱先生在另外一篇文章中的说法是两万件),而经过整理研究的标本只有818件。从报告中能够看到图像的只有30件(包括线图标本30件和图版照片29件,从石制品的研究来看,各个类型的数量不清,石核、石片分类描述一笔带过;石器研究分类简单、随性、不精确。

峙峪遗址石制品
我们应当庆幸,贾兰坡先生不愧为中国旧石器考古学的开拓者和建造者。试想如果不是他率领团队完成了《山西峙峪旧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可能峙峪遗址就永无面世的机会了!想到这里我真有点后怕。尽管这个19页的发掘报告,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毕竟给我们留下来一副比较完整的“满月照”——峙峪遗址永远定格在1972年的状态。
峙峪遗址从1972年面世到如今,所有关于峙峪遗址的介绍,无论是教学用书还是其他综述性文章均以此为本底,无一例外。
三、价值几何
峙峪遗址已经50岁了,还是一张刚满月时的“婴儿照”。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体制、学术传统、人为因素等,要找“托词”很多,也很容易;最关键的还是对峙峪遗址的价值认识不到位。衡量一个遗址的价值,应该说是在发现之初就应该做的最重要的工作。但到目前为止,我国的旧石器遗址均缺少这样一个步骤。

峙峪遗址含有灰烬的地层
首先,是遗址性质定位问题。
峙峪遗址是中国继北京人遗址之后发现的用火遗迹最丰富的一个遗址,海量的文化遗存和特殊地层堆积所承载的人类活动信息堪与北京人遗址媲美。但峙峪遗址是属于河流相堆积,这是与周口店北京人遗址最大的不同,过去国内学者多半认为河流相堆积的旧石器遗存不能叫遗址而只能称之为地点。因此,峙峪遗址发现的巨厚灰烬层并未引起学术界的重视。
其次,是后续研究和信息解读的问题。
1972年的《山西峙峪旧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发表之后,有关峙峪遗址的研究基本停滞了,无论教材还是其他综述性论文或书籍,有关该遗址的认识都在“原地踏步”。仅有《峙峪遗址刻划符号初探》、《峙峪遗址碎骨的研究》两篇论文和《黑驼山下猎马人》一篇科普作品。这些文章虽然提供了一些“发掘报告”未曾涉及的信息。然而,还有大量重要信息没能被解读出来。

残破的峙峪遗址剖面
最近为了写一篇与峙峪遗址相关的文章,仔细研读了这份发掘报告,从中读出了一些非常重要的线索:① “石器制品和动物骨骼碎片集中分布在厚达0.9-1.5米厚的灰色、黑灰色、褐色亚砂土和灰烬层中。”表明峙峪遗址是周口店北京人遗址之后发现的又一个具有大型用火遗迹的遗址;而且是一个“多年生”、“累次使用”的旧石器时代遗址;② “文化层底部的灰烬层呈透镜状分布,其中含有大量石器、动物化石以及少量有烧过痕迹的砾石。”表明峙峪遗址很可能具有“火塘”结构; ③ “化石密集成层,一般保存情况较差,未见头骨,下颌骨多残破,大多数是单个的牙齿和被击碎的骨片”表明这里是峙峪人“肢解”、“分享”、“烧烤”猎获动物的营地。当然还有最重要多一点就是“在峙峪动物群中有蹄类所占的比例最大,种类上占70%,数量占95%以上,构成这一动物群的主要部分,其中典型的草原动物有蒙古野马、野驴、普氏羚羊、鹅喉羚等……根据马类的右上第三臼齿计算,发现的4000余枚马类牙齿至少代表了近130匹野马和90头野驴”被誉为“猎马人”。这一点早在1972年的研究中就提出来了,但后来的跟进研究缺失,导致我们只能停留在“猎马人”的想象中,原始人是如何猎取马类这种大型动物的?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可以去追踪,可惜不但当时原有的研究团队没有做,其他人也没有做。

潘色旺遗址博物馆俯瞰

潘色旺遗址发掘地层剖面
峙峪遗址在很多方面可与法国塞纳河边的潘色旺遗址相比。2002年在《华夏考古》上看到有关潘色旺遗址文章的时候,就在想:法国人真运气,这么好的遗址让他们给碰上了!但是试想一下,这样的遗址如果放到中国是什么后果?我真的不敢往下想。或许和峙峪遗址一样,甚至有可能还不如峙峪遗址呢。

潘色旺遗址博物馆展出的遗址复原场景
四、谁之错
笔者曾在《中国文物报》发表的《旧石器考古发掘研究与保护的思考》一文中指出:中国的很多旧石器时代遗址都是在短暂曝光之后就进入了可悲的沉寂,在一两篇“发掘简报”或学术论文发表后就“刀枪入库”、“马放南山”,虽然在“行政管理” 上建立了“四有档案”,但在“学术活力”和“社会影响力”上,很多已“名存实亡”。如果一个遗址,十年没有一次发掘,没有一个相关课题,没有一篇学术论文,甚至没有一次面对公众的展示,应该说这个遗址“死了”。峙峪遗址也是这样,虽然冠以了“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但我们对峙峪遗址的认识还停留在上世纪70-80年代的程度上。

峙峪遗址现状
这是中国旧石器时代遗址甚至后段考古中比较普遍的一种现象。发现遗址就像一个婴儿诞生;“发掘报告”或“发掘简报”就相当于它的“满月照”,也是它的“终身照”——被永久定格。还有很多遗址连一张“满月照”都没有就夭折了。这凸显了我国在文物考古和文化资源管理上与先进国家的莫大差距。
谁之错?显然不是哪一个人,哪一个团体的问题,也不是一个局部问题,而是全方位的。其中包括体制、管理、人才、发掘理念等众多方面。发掘方法、研究方法老套,习惯成自然,习惯势力和习惯思维,造就了习以为常、混沌不觉的田野模式。像中国式过马路一样,成为一个难题。
五、中国式考古难题
考古学更多的像考古发现学,特别是墓葬发掘,精美的器物、墓志发现之后,历史、环境、社会等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剩下的工作就是进入博物馆,周游列国、巡回展览而已。这种大环境也会影响到旧石器、影响到史前考古。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从法国和欧美发达国家的考古模式来看,他们的理念是经营遗址;把遗址看作“文化遗产”来发掘、研究,并依托遗址建立博物馆来展示远古人类的生活状态和文明进程。
首先,有一个大家共同遵循的操作规范。这种规范并非强制性的行政命令,而是考古学家在长期的考古实践中,优胜劣汰形成的最优方法。换言之,他们怀着强烈的事业心和职业精神,以保护历史文化为己任,博采众家之长相互借鉴,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种共同遵循的考古规范。法国人做考古,从发现开始就将遗址的保护纳入发掘研究的范畴。他们会用几年的发掘来探究、衡量这个遗址的考古价值,继而进行持续不断的发掘研究,将遗址的发掘、研究、保护与展示有机结合起来。
其次,是核心团队和人才培养机制。在法国,考古工地就是最好的田野考古学校。重要的旧石器遗址,一般都会建在一个大的实验室或博物馆。考古发掘一般选择在大学放假期间,从各个大学招募热爱考古的的大学生和考古专业的本科生、硕士生,在主持发掘技术人员指导下,严格按照既定的考古流程和操作规范进行考古发掘和资料整理。
态度决定命运,细节决定成败。通过峙峪与潘色旺的比较,最直观的比喻就是:囫囵吞枣与细嚼慢咽。前者消化不良导致面黄肌瘦,后者吸收良好养得“膘肥体壮”。我们试图找到中法旧石器考古学之间的差距和解决问题的办法。在法国,把考古发掘当作侦探破案——破一个千古大案,所以用几十年仔细发掘,寻找曾经发生的每一个细节。在中国,考古发掘是为证明历史服务的,遗址被看作历史文化的证据,并引以为傲。可以说这种理念上的差异是致命的。
我们承认中国旧石器考古的“学术规范”与世界先进国家之间存在很大的差距,但要探讨其中原委,就不得不说到“管理体制”的问题。在法国,从遗址发现、发掘,到保护、研究与展示的“一条龙”考古模式,除了学术素养和学术规范之外,考古学家有充分的自由度,只要论证其重要性,政府或财团就会给予全力资助。在中国,按说“举国体制”下的考古应该有更大的优势——遗址博物馆也不是新生事物。考古发掘、文物保护、博物馆展示三者兼容并存并不是没有先例,像半坡博物馆、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就是这样。仅从这一点就可看出我国文物考古学科发展上,在历史考古和史前考古两方面的关注程度和不均衡性。同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周口店遗址”和“秦始皇陵及兵马俑坑”,其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不分伯仲。显然,历史阶段的考古项目更容易看得懂、更能吸引社会关注,导致一个门庭冷落、一个人气爆棚。因此,学术界和文物主管部门,应当从“学术价值”和“政策倾斜”两方面共同提升史前遗址的社会关注度,使峙峪遗址这样有价值的、有代表性的遗址更好地被社会所认识。

周口店遗址博物馆

西安半坡博物馆

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峙峪遗址的命运有其历史原因和必然性。我们在为峙峪遗址呐喊也是在为中国的旧石器考古遗址呐喊。
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我们希望峙峪遗址的遗憾不再重新演!
(来:《化石》2015年第2期)
标签: 考古遗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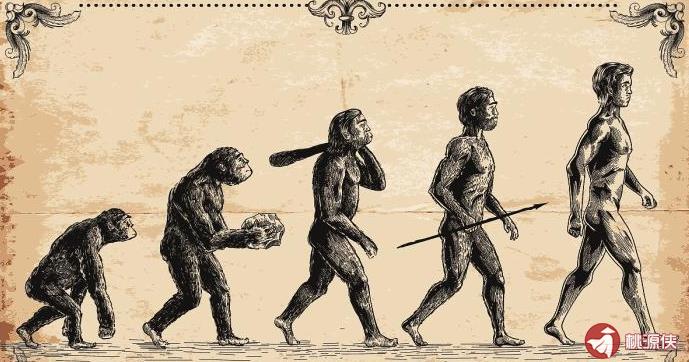

还木有评论哦,快来抢沙发吧~